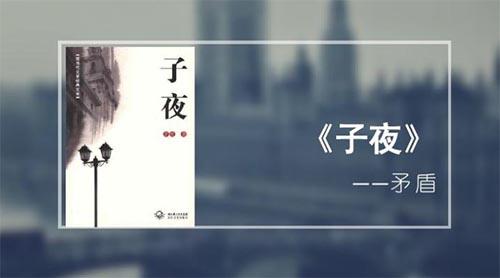——讀《子夜》有感
文學(xué)巨匠茅盾的小說《子夜》,以居高俯瞰的視角,以20世紀(jì)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軍閥混戰(zhàn)、工人罷工的舊上海為背景,社會(huì)現(xiàn)實(shí)紛繁萬狀、忽閃忽逝。以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為中心,展現(xiàn)了社會(huì)生活的廣闊畫卷。
故事的主人公吳蓀甫是一個(gè)失敗的“英雄”。他出身世家,游歷過歐美,學(xué)習(xí)企業(yè)管理方法,他的理想是發(fā)展民族工業(yè),在中國實(shí)現(xiàn)資本主義。但吳蓀甫過于剛愎自用、驕傲自大,不聽他人勸誡,一意孤行,他的夢(mèng)想覆滅了。
在我看來,吳蓀甫的失敗分為內(nèi)因和外因。
內(nèi)因便是他不會(huì)為人處事的性格。他手下有一幫得力干將,譬如屠維岳、莫干丞、高升一干人。他們雖不是死心塌地,絕對(duì)忠誠地為他辦事,但也不會(huì)因?yàn)樾″X小事而背叛他,而吳蓀甫卻不相信他們,最終不能成事。又比如說杜竹齋、王和甫等眾人想與吳蓀甫合作,而吳蓀甫卻認(rèn)為單憑自己的力量就能使工廠達(dá)到頂峰,最終他們只得灰心而走,或冷眼看世,或投奔他人。吳蓀甫也因?yàn)橘Y金短缺,降低工薪激怒了工人們。
他只想被別人一聲一聲的叫著“吳三爺”長“吳三爺”短,而不想與別人合作,更不想被別人批評(píng),這就是他自身最大的弱點(diǎn)。
吳蓀甫失敗的外因有兩點(diǎn),其一便是周圍對(duì)手的競(jìng)爭(zhēng),最厲害的莫過于是趙伯韜了,趙伯韜是他在公債場(chǎng)上的對(duì)頭,是公債的多頭,所謂多頭便是從事商品、有價(jià)證券交易的人預(yù)料貨價(jià)將漲,而買進(jìn)現(xiàn)貨或期貨伺機(jī)賣出。相比之下,吳蓀甫所代表的空頭就要遜色很多了。而趙伯韜又總是想使吳蓀甫的夢(mèng)想不能實(shí)現(xiàn),這使吳蓀甫非常氣憤,卻又因無法解決而無奈。
其二便是時(shí)代的限制,這是一個(gè)民族工業(yè)生不逢時(shí),注定要失敗的時(shí)代,主要體現(xiàn)在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(jí)的束縛,以及連年的軍閥混戰(zhàn)。
吳蓀甫在政治經(jīng)濟(jì)上的軟弱無能,表面的果斷堅(jiān)決背后是胡亂猜疑,充滿自信的背后是悲觀絕望,胸有成竹的背后是驚慌失措。他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。
吳蓀甫創(chuàng)立產(chǎn)業(yè)處于世界經(jīng)濟(jì)危機(jī)的大背景下,競(jìng)爭(zhēng)對(duì)手趙伯韜又以世界第一經(jīng)濟(jì)大國美國為后臺(tái),這說明吳蓀甫的失敗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有直接的關(guān)系。他感到無法抵抗壓力,無法振興工業(yè),越發(fā)的悲催和消極,底氣不足。他既受到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主義的排擠,又拼命的殘酷鎮(zhèn)壓工農(nóng)群眾,這是當(dāng)時(shí)民族資本家的典型特征,也是吳蓀甫最后悲劇的客觀因素。
由此可見,這是一個(gè)時(shí)代的悲劇。
若沒有戰(zhàn)爭(zhēng)的硝煙,沒有專制的桎梏,沒有罷工的陰影,沒有外來的侵略,吳蓀甫,這個(gè)民族工業(yè)的時(shí)代驕子,有可能把夢(mèng)想變?yōu)楝F(xiàn)實(shí)。
子夜難行,而有人在前行!
同在這個(gè)時(shí)代,共產(chǎn)黨卻是與廣大工農(nóng)群眾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,在子夜中摸索前進(jìn),19年后,鮮紅的五星紅旗飄揚(yáng)在天安門廣場(chǎng)。